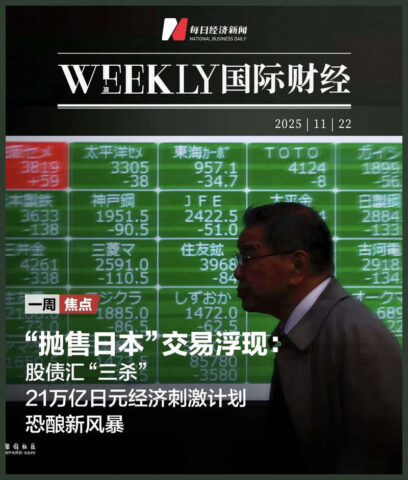近日,彭博社、路透社等国际权威媒体披露,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前夕,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(UAC)正式签署联合研制协议,计划共同开发一款可容纳100名乘客的SJ-100双引擎窄体客机。尽管印方已确认协议签署,但关于技术转让条款、投资分配比例等核心要素,双方均未对外公布具体细节。这一动向迅速引发国际航空产业界的深度关注。
时间回溯至2023年,中俄CR929宽体客机项目曾因技术路线分歧宣告终止。
该项目始于2016年,中俄双方基于互补性需求展开合作:俄方希望借助中国资金与市场实现航空工业转型,中方则看重俄方在复合材料领域的深厚积淀。
然而,在动力系统选择上,双方产生根本性分歧——俄方坚持采用自研PD-35发动机(推力34吨),而中方长江-2000发动机(推力35.2吨)已取得关键突破。
更深层的矛盾在于项目主导权争夺:俄方试图掌控总体设计与供应链,中方则要求扩大技术参与度,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项目解体。
尽管俄方曾表态将以供应商身份继续参与,但中方已明确转向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。
CR929项目终止后,中国商飞迅速推进C929独立研发进程。
该机型定位为波音787、空客A350的直接竞品,计划2030年实现首飞,2045年前完成1000架交付目标。
值得关注的是,在2024年初的莫斯科航展上,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虽表示愿向中国提供PD-35发动机技术用于军用运输机改装,但明确排除重启CR929合作的可能性。

俄媒分析指出,受俄乌冲突导致的西方制裁影响,俄罗斯航空工业面临零部件断供与资金链断裂双重压力,PD-35发动机研发进度已滞后三年,而中国C919客机的成功商业化进一步削弱了俄方合作价值。
从产业格局演变看,俄罗斯正经历战略收缩。
在CR929项目中,俄方从联合研发方退居为技术供应商,仅负责复合材料机翼等非核心部件生产。
这种转变折射出全球航空产业链的重构: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庞大的内需市场,正在重塑技术标准与市场规则。
数据显示,中国民用航空市场未来20年将需要8000架新飞机,这个数字相当于当前全球在役飞机总数的15%。
反观俄印此次合作,历史教训似乎未被充分汲取。
双方延续了中俄合作中的”技术换市场”模式,但存在三大隐忧:
其一,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虽在军用航空领域有所建树,但民用客机制造经验几乎为零,其生产的”北极星”直升机曾创下坠机率纪录;
其二,印度营商环境在世行评估中排名靠后,政策连续性、合同执行效率等关键指标存在缺陷;
其三,俄罗斯航空工业当前深陷供应链危机,2023年民用飞机产量同比下降42%,技术输出能力已大不如前。
值得玩味的是,俄罗斯在合作中的战略定位出现微妙变化。
相较于对华合作时的技术主导诉求,此次俄方对印合作更强调市场准入与资金支持。
这种调整反映出俄罗斯航空工业的困境:在西方制裁与自身技术迭代滞后的双重挤压下,不得不通过分散合作对象来维持产业存续。
但历史经验表明,航空制造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,缺乏核心系统集成能力与持续研发投入,单纯的市场换技术模式难以成功。

从地缘经济视角观察,俄印航空合作具有双重战略意义。
对俄罗斯而言,这是突破西方技术封锁、维持航空工业全球地位的重要尝试;对印度来说,则是获取先进航空技术、实现”印度制造”战略的关键跳板。
然而,双方在合作框架设计上存在根本性矛盾:俄方希望保持技术主导权以获取更高利润分成,印方则要求通过本地化生产实现技术转移。
这种结构性冲突在中俄合作中已得到验证,在文化差异更大、产业基础更弱的俄印之间,矛盾可能更为突出。
当前全球航空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,中国通过C919/C929项目构建的自主技术体系,已形成涵盖设计、制造、适航认证的完整产业链。
相比之下,俄罗斯航空工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18%萎缩至2023年的7%,印度则尚未建立完整的民用航空产业生态。
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,或许预示着未来国际航空合作将更多呈现”中心-外围”结构,技术主导方与市场提供方的博弈将更加激烈。

俄印航空合作协议的签署,既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,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缩影。
当技术迭代速度超越国际合作磨合周期,当市场规则重塑快于战略伙伴关系调整,任何合作都需面对更严苛的可行性检验。
这场跨越欧亚大陆的航空产业实验,其成败不仅关乎两国工业命运,更将为新兴经济体突破技术壁垒提供重要参照。
在航空制造业这个考验综合国力的竞技场上,真正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。